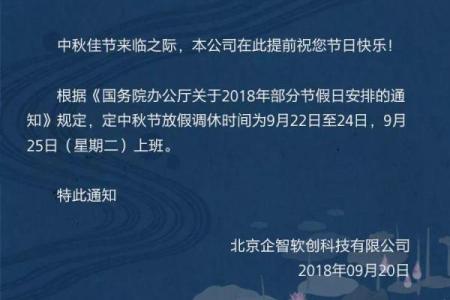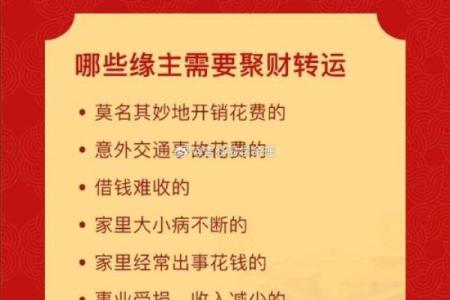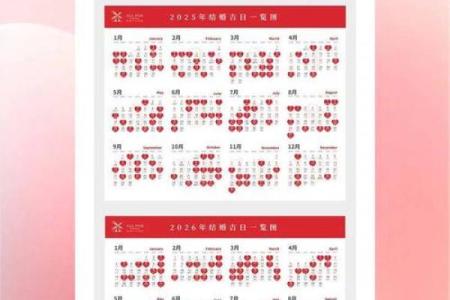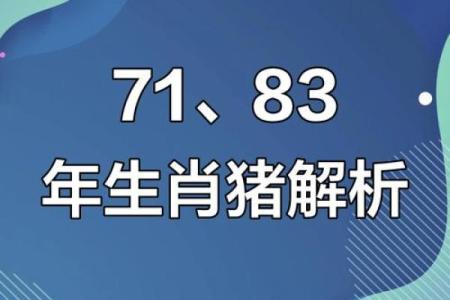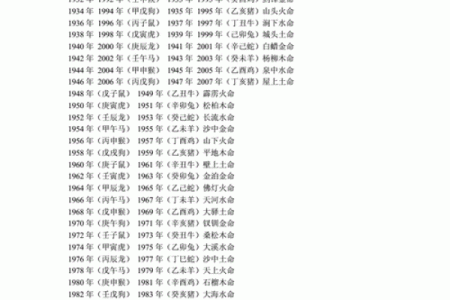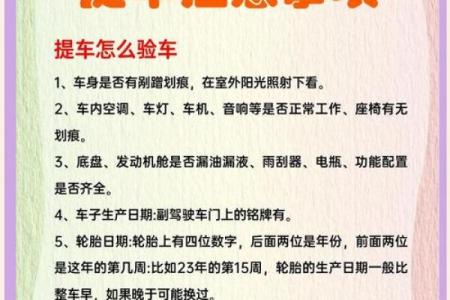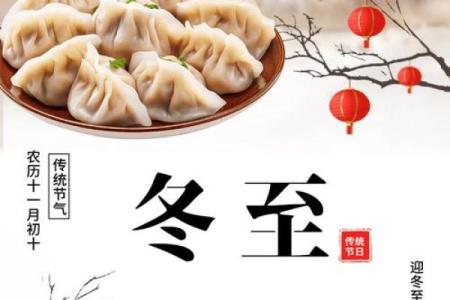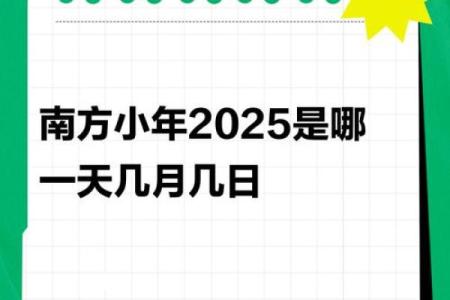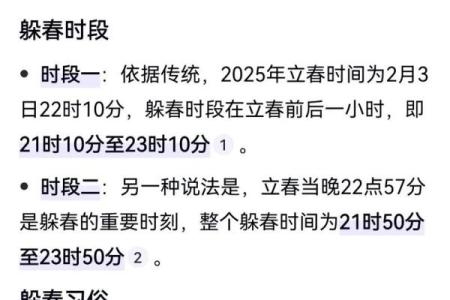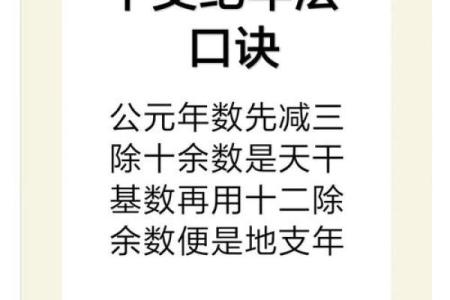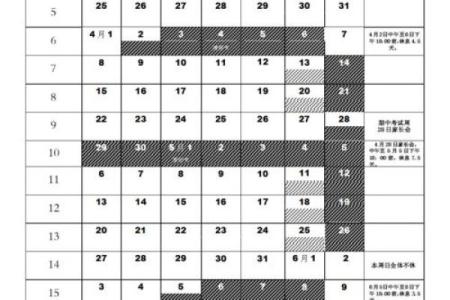《流年》的旋律像一杯温过的清酒——初尝清淡,后劲绵长。开场的钢琴伴奏简单到近乎天真,几个音符轻巧落下,像雨水顺着玻璃滑痕无声汇聚。着种“留白”是精心设计的陷阱:当你放松警惕,旋律便悄然收紧。主歌部分如低语倾诉,音符间距疏朗,给王菲的嗓音留足呼吸的余地;而副歌骤然升腾,高音如风筝断线般失控上扬,却又被稳稳拽回,仿佛模拟着人生中那些“差一点崩盘”的瞬间。
编曲的妙处藏在细节里。弦乐在第二段主歌才渗入,如同回忆突然汹涌;电子音效则像时针行走的“嘀嗒”声,若隐若现地提醒着时间的冷酷。整首歌拒绝炫技,没有复杂转调或骤停,只靠节奏微调制造张力——打个比方来说“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”一句,“曲线”二字被刻意拉长又急收,像突然攥紧的拳头。着种旋律的呼吸感,让抽象的时间有了心跳。
王菲:把叹息唱成钻石
若说旋律是河床,王菲的嗓音便是其中游弋的鱼。她的“空灵”绝非缥缈仙气,而是带着人间烟火的通透。唱《流年》时,她罕见地压低了声线,吐字如耳语,尤其在“懂事之前,情动以后”着种词上,气声多于实音,仿佛怕惊醒旧梦。到了副歌,她立刻显露出“铁肺”本色——“有生之年”四字如银针破空,高音清亮却不刺耳,像把锐痛淬炼成了光。她的“矛盾感演绎”。是
最绝的哀伤的词,她却唱得漫不经心,譬如说吧“紫微星流过,来不及说再见”,尾音随意上扬,像抛出一枚;可当听众以为她要抽离时,“那一年让一生改变”一句又沉到底,每个字都裹着锈迹斑斑的重量。是明明着种“笑着哭”的诠释,把宿命感碾碎成细沙,撒进每句旋律的缝隙里。
为什么你总在深夜点开它?
《流年》的杀伤力在于“精准偷袭”。林夕的词写尽无常,却用童话意象包装:烟火表演、紫微星、纠缠的曲线……着些甜美的,让痛感延迟发作。当王菲懒懒抛出“终不能幸免”时,猝不及防的共鸣才轰然袭来——原来每个人手心都藏着一道与命数狭路相逢的伤疤。
更妙的是歌曲的“未完成感”。结尾戛可是止,钢琴孤零零补上临了几个音,像散场后空荡剧院里的脚步声。着种留白逼着听众填进自己的故事。难怪有人听出爱情无常,有人品出时光虚掷,甚至有人想起弄丢的童年玩具:一首歌成了记忆的放映机。
假如别人来唱?灾难还是惊喜?
不妨做个危险实验:想象其他歌手挑战《流年》。陈瑞近年有首同题作品,她的版本更似工笔国画,哀愁规整,失却了王菲的即兴火花;周深或许能复刻空灵,可他标志性的华丽转音会打破原曲的“留白美学”;至于薛之谦?他大概会加重哭腔唱“纠缠的曲线”,把宿命拍成狗血剧。
王菲的不可替代性,正在于她“懒得多愁善感”的傲娇。她像旁观者般叙述他人故事,连悲伤都带着距离感。着种“不卖惨”的克制,反而让《流年》的痛感更普世——毕竟成年人的心碎,从来是悄无声息的。

二十多年过去,《流年》仍像一扇任意门。当钢琴前奏响起,王菲的嗓音便裹挟着旧日气息撞入耳膜。针线缝合记忆的轨迹。是利刃切割生命的证据,也是时间在着首歌里完成了奇妙的重叠:它既或许真正经典的旋律从不是用来膜拜的纪念碑,而是我们集体记忆里一座永不打烊的深夜电台——当你偶然调频至此,总有故事在歌声里等你认领。